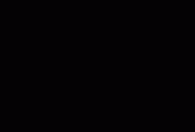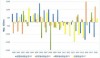2017年的今天,奢侈品牌LouisVuitton(LV)和街头潮牌Supreme在巴黎男装周上正式发布合作款。消息早先已经在Instagram上流传,先是Supreme粉丝发了张织满LV和Supreme纹样的毛衣,接着是LV男装设计师发了张Supreme的贴纸并且秒删。外界的猜测终于在男装周第一天得到证实。
今天是 2019 年 1 月 19 日,这一年的第 19 天。
在 Google 上搜索 “LV and” 这个词组,第一条搜索建议会是什么?
答案是 Supreme。
2017 年的今天,奢侈品牌 Louis Vuitton(LV)和街头潮牌 Supreme 在巴黎男装周上正式发布合作款。消息早先已经在 Instagram 上流传,先是 Supreme 粉丝发了张织满 LV 和 Supreme 纹样的毛衣,接着是 LV 男装设计师发了张 Supreme 的贴纸并且秒删。外界的猜测终于在男装周第一天得到证实。
这场合作让很多人感到意外,最直接的理由就是两家的历史过节。Supreme 曾于 2000 年推出结合 S 和 LV 图案和画板和服饰,被 LV 起诉后不得不下架。
LV 和 Supreme 似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群体与场域:一个是以巴黎时装屋为大本营的奢侈品牌,一个是张扬青年亚文化的街头服饰。但时尚从来都是易逝、流变的。从 Marc Jacobs 到 Nicolas Ghesquiere,两任 LV 创意总监都热衷于跨界,后者更直白地表达过“在街头展示奢侈风格”的兴趣。
消费者也是善变的——包括“谁是消费者”这件事。根据贝恩咨询去年给出的展望,到 2025 年,Z 时代和千禧一代(差不多对应中国的 80 后到 00 后)对全球个人奢侈品市场的贡献率将突破 50%。他们像上一代掌握时尚界的知识,在意身份,把排长队当作一种仪式;他们热爱 logo,而 Supreme 简直把 logo 用到了极致;他们活跃在社交网络,对潮流的回应更敏捷,这部分解释了,为什么 LV 和 Supreme 的合作最早会在 Instagram 这个属于年轻人的平台上曝光。
新的、更年轻化的消费者结构,新的传播方式和消费模式,都在模糊奢侈品与潮牌、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界限。LV 和 Supreme 的合作更像是水到渠成而不是石破天惊,毕竟前者早就把村上隆设计的图案印在了纽约第五大道的旗舰店上,而村上隆的艺术,怎么都谈不上高雅。
“我只是觉得它们(Supreme)的形象和 Louis Vuitton 的形象放在一起很完美,有一种流行艺术的感觉。”
Kim Jones,LV 艺术总监
2017 年,LV 和 Supreme 的联名款在全球多家快闪店销售,据称卖出了 1 亿欧元,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凯雷集团(The Carlyle Group)同年买下了 Supreme 的部分股权;去年,两家的合作继续;今年的合作情况暂未披露。
但 Supreme 也不再是 LV “放下身段”的唯一标志。去年,LV 请来了 Virgil Abloh 作为男装艺术总监,后者的成名作正是街头潮牌 Off-White。今年 1 月初,他为 LV 带来的新系列在东京一家快闪店亮相,头 48 个小时就比 LV 与 Supreme 联名款去年同时段的销售量高出了 30%。
去年底,《好奇心日报》梳理了奢侈品市场的新动向,文章值得一读。
此外还有:
从“汉城”到“首尔”
2005 年的今天,时任汉城市长李明博宣布将这座韩国首都的中文名由“汉城”改为“首尔”。变化首先体现在汉城市的中文网站上,中国方面随后也予以配合。
根据李明博的说法,“首尔”更接近国际通用的 “Seoul” 的发音,也在字面上体现了“首都”的含义。由于历史原因,朝鲜语中同时存在“汉城”和“首尔”的说法,但在中文中对应的是同一个词“汉城”,改名也有利于避免通信中的误解。
中国舆论对韩国首都改名反应不一。一些人指责改名的政治色彩,猜测其真实动机是强调韩国的民族独立性;也有人认为应当尊重本地语言的音译和本地人的自主权。
西沙海战
1974 年的今天,经过几天的对峙,中国与南越海军在南海永乐群岛一带交火,中国海军在两天之内即取得速胜。
永乐群岛是西沙群岛的一部分,二战后由中国管辖,但越南亦声称对其享有主权,一度占领了其中的多座岛屿。1974 年 1 月中旬,中国与南越对永乐群岛展开争夺,最终于 19 日清晨爆发流血冲突,中国在当天的海战中成功守住了已有驻军的岛屿。此时,邓小平提议扩大战果,中国海军接着通过 20 日的夺岛战役,夺回了南越 1956 年后占据的全部三座海岛。这被认为是中国海军对外作战中的首场完胜。
生日快乐,戴乃迭
如果说《离骚》《牡丹亭》《儒林外史》《红楼梦》《鲁迅选集》《青春之歌》《芙蓉镇》这些从古典到现代的中国文学作品有什么相同之处,答案可能是:他们的英文译者名单里有固定一对名字:杨宪益和戴乃迭。
1919 年,翻译家戴乃迭(Gladys Yang)出生于中国北京,今天是她的百岁诞辰。
戴乃迭生于一个英国传教士家庭,她的母亲在海淀从事神职工作,父亲在燕京大学教授经济学。她和父母一同住过燕南园,逛过庙会,游览过北戴河的海滩,会在母亲升起“米字旗”时回到一家人度假的小屋吃饭。当她在童年时代踏上英国土地时,她依然不会说中文,但“中国”一词将伴随她的一生。
1937 年,戴乃迭进入牛津大学,专业是法国语言文学。她在那里遇到了一个研究西方古典学的中国人,1915 年出生的杨宪益。他们一起谈论中国,抗议日本的侵略战争,一同参与传统的划船活动。当戴乃迭以未婚妻的身份随杨宪益回到中国时,她已经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中文学士。这桩婚事并没有获得戴乃迭家人的全力支持,但它在战时重庆的知识界却是一件盛事。
戴乃迭和杨宪益的翻译工作有两个黄金时期,一个是 1950 年代,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初。他们将不同时代、不同文体的汉语经典引介到英语世界,包括《红楼梦》《离骚》这样的巨著和 1976 年后那些更具时代气息的作品。
但在 1968 年 4 月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之中,他们被卷入一场莫名的英国间谍案而分别入狱。戴乃迭后来说,四年时间里,她成了《资本论》在全世界最快乐的读者——因为这是狱中仅有的读物之一。她依然保持着尊严,而她并不知道自己孩子的处境。她唯一的儿子杨烨后来患上了精神病,在伦敦修养期间自焚身亡。
生命中的最后几年,戴乃迭不再频繁地出门、写作,情绪也变得压抑,尽管她依然会用微笑迎接造访的亲朋好友。1999 年 11 月 18 日,戴乃迭去世。此后十年,直到去世,杨宪益也不再从事翻译工作。
编辑:alushazi